

阿诺德·汤因比是著名的历史学者展鹏配资,他的《历史研究》等作品影响深远。他对人类历史上的城市给予了很多关注。2021年,他的《变动的城市》被译为中文。今年,他主编的《命运之城》也在近期出版中译本。这部作品书写了人类历史上19座伟大的城市样本,从雅典的城邦到长安的盛世,从威尼斯水城到纽约都市……揭示了“城市是人类灵魂安放之所”的深刻命题。
每一座城,都是一个熟悉又陌生的“想象的共同体”。我们建造了城市,城市也在无形中改变着我们。而关键在于——我们如何想象城市?想象是双向的:既指向过去,通过文字触摸那些消逝的伟大城市;也指向未来,思考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城市,人与城应该建立何种关系。
近日,在上海图书馆东馆,新京报书评周刊、光启书局联合邀请了《命运之城》的译者、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教授陈恒,同济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教授张松,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罗岗,开启一场由“城市罐头”主播姚嘉伟主持的对谈活动,共话人与城的相互成就。
以下为对谈整理,有删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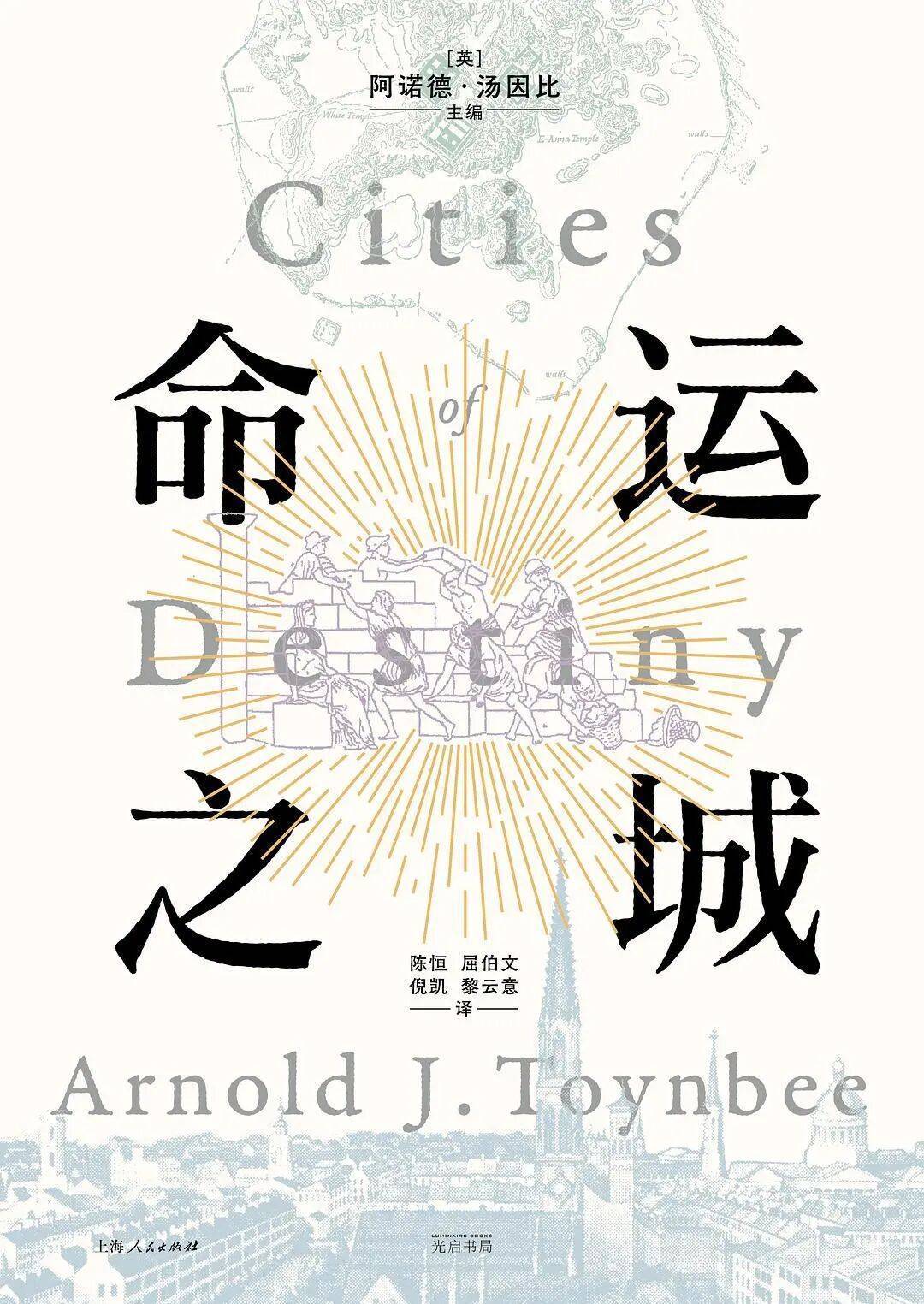
《命运之城》,[英] 阿诺德·汤因比 主编,陈恒、屈伯文、倪凯、黎云意 译,光启书局,2025年10月。
整理|刘亚光
我们现在依旧没有走出“城市病”
姚嘉伟:首先请本书主要译者陈恒老师介绍一下汤因比以及这本书。因为包括像我在内的年轻一代其实对汤因比还是比较陌生的。可以请您讲一讲他的生平和这本书在他学术写作生涯里的一个位置吗?
陈恒:这本实体书大概是我在十年前无意中知道的,今天大家看到的这本书是小开本,它的英文原版大概有中文版的两倍大,比《辞海》还要大三分之一,插图也特别多。我当时打开一看出版的年代是1967年。
当年我们在读书的时候,这部书对我们来讲好像是一部非常神圣的著作,对我们每个人的影响都非常大。因为汤恩比不仅影响了历史学,他的著作跨越历史学,对整个思想史、文化史,包括后来新出现的城市研究和城市史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而且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那就是很勤奋。他的写作年龄大概在70年,从他最早的著作一直到1976年。为什么说1976年呢?因为他在1975年去世以后,身后有一本非常有名的著作《人类与大地母亲》,是他去世以后别人帮他整理出版的。
[英] 阿诺德•汤因比 著
徐波 等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年8月
除了他的贡献巨大外,我认为汤因比一生的写作有三个阶段。早期他是做古典学出身,研究国际关系,做了大量的调研报告。到了20世纪30年代,他专心写他的伟大著作《历史研究》。美国《时代》周刊在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称之为先知式的知识分子,所以从上个世纪60年代以后,到了晚年他的写作路径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侧重于从道德的角度、宗教的角度来考虑世界、考虑人类。所以他的整个思想是非常宏阔的,而且在理论上的贡献也非常大。
汤因比第一个重要的贡献,是他跨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在这之前都是以西方为中心的民族国家叙事。另外一个贡献,就是所谓挑战和应战。他认为文明的出现在极端的环境下都不太好,无论是极端的优秀也好,极端的恶劣也好。他在适中的位置,挑战应战了很多世界文明的产生。他把这些思想具象化在《命运之城》这本书里,找了一个非常具象化的概念是城市。他的一些研究思想实际上都是通过这本书中的一个具体的城市表达出来的。
罗岗:这本书面向的是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读者,当时有城市病,城市面临着许许多多的新问题,这些新问题怎么来解决就变得很迫切,而且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他说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要回顾历史。
比如说,书里有两幅图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一个是古代雅典的图,步行15分钟城市的各个地方都可以走到。第二个是纽约曼哈顿,中央车站前面巨大的人口流动,通勤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步行15分钟可以走到各处的城市,是你马上就能知道这个城市是什么样的,能在脑子里用脚步去丈量的。但是对巨型城市,你根本不知道它是什么。就像我们生活在上海展鹏配资,我们知道上海是什么吗?你怎么去描述它呢?可能你只能描述地标性的建筑。你在南京路,或者是东方明珠塔,或者是经贸大楼,或者是城隍庙宇,你没有办法完全在感知的尺度上来把握这座城市。这些问题我想是这本书的每一个读者都可以切身体会到的问题。
电影《美国往事》(1984)剧照。
我们现在并没有走出城市病的这些问题。所以这本书让我觉得很有现实意义。因为中国正在大规模地城市化,我们的城市也在迅速地发展。这是虽然这本书从1967年出版到现在已经有差不多60年的时间,但是把这本书翻译过来依然没有过时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姚嘉伟:这本书的最后一章写未来的城市——普世城,对这个普世城的概念进行一个有点寓言式的写作,其实是他们在60年代对于当前城市的反思,对于城市发展模式的一个新的构想。现在已经过去了很多很多年,在他们之后,各种各样的建筑跟城市思潮也风起云涌。以张老师做城市规划这些年的经验来看,您怎么评价这一章?
张松:我觉得他的预测还是很到位的。他认为城市是走向普世化的。实际上我们现在纽约跟上海,跟北京都没什么区别,就是从城市的外观,城市现代化基础设施和人的活动交往模式等都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城市面临非常大的问题,比如气候变化、能源危机、种族冲突等。现在还有一些城市有战争。我们当下就是各种建设性破坏很厉害,以发展、以未来的名义对过去进行彻底的破坏。
欧洲包括美国一些城市做得还是可以的。他们在20 世纪60年代就开始制定法律,比如《马尔罗法》。马尔罗是法国文学家,当然也是政治家、外交家。他制定了一个法律,老城区都不能按现代主义的规划,你把它空出来,按照原有的尺度、原有的记忆、原有的密度、原有的多样性来保护。我们有很多人也愿意去欧洲旅游,欧洲的很多小城,包括意大利就觉得很浪漫,以为人家是石头的,我们是木头的。不是这样的。其实他们是有一套法律,就是在开发建设新城的时候,对老城市保护更新活化利用。
作为“想象之物”的城市
姚嘉伟:罗老师也是长期的写作,关注城市文化。罗老师在早年的著作《想象城市的方式》里面有谈到城市不仅是空间,更是被想象、被观看、被书写的场域。想请您谈一谈您的这个观点有没有在这本书里面得到一些体现,或者说您对这个的看法。
罗岗:汤因比把城市看成一个文明的载体,是一个想象之物。为什么这样讲呢?他在这书里面讲到,大规模的人口聚集并不是城市,城市是要有灵魂的。比如“歌德的魏玛”,对不对?魏玛是用歌德来命名的,当然实际上《歌德的魏玛》不仅仅讲的是歌德一个人,而是那一代人。在魏玛时代,德国启蒙运动的一代大师都在那个时候出现,他们定义了这个城市。如果说空间是一个物理性的存在,要通过人类的各种各样的活动把它再现出来,而不是一个死的空间。再现出来要通过主观和客观、精神和物质、客体和主体的,人类透过自己各种各样的创造活动和固有的物质性存在之间产生密切的互动,创造出一个新的东西,这就是城市。
姚嘉伟:刚才罗老师有讲到很多人关于城市的想象,这个机制具体是如何运作的。这会让我想到很经典的情境主义的实践,如何对抗资本主义,这其实跟我们现在的城市生活也密切相关。罗老师,您能不能聊一聊这样的方法实践,通过我们阅读像《命运之城》这样的历史文本,对于我们的城市生活可以起到怎么样的启发?
罗岗:情境主义实际上也和建筑学者简·雅各布斯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有很大的关系。我在纽约的时候,那时候纽约大学有一个教授,自称为雅各布斯主义者。他规定他的学生不准去亚马逊上订书。当时在纽约大学边上有一个莎士比亚书店,他特别去跟那个民营书店的人说好,我们今年上这个课,有什么参考书、要订多少本,学生必须到这个地方去买。如果做不到就不能选课。另外,他喝咖啡从来不喝星巴克,如果在课堂上看到学生带了星巴克来,他要怒目而视。这就是我们说到的情境主义或者日常生活的实践。现在大城市讲的是功能性规划,其实街边的邻里空间关系全部都破坏了,没有什么街坊邻居了。很多年轻人从来都不去超市、街上,更不要说去杂货店里买东西,可能所有都是网购。雅各布斯提倡的就是城市规划的多元性,要打造“漫步城市”。城市可不可以成为一个步行城市,是人和城市之间互动的一个很重要的衡量标准,或者说城市是不是宜居的一个标准。
电影《书店》(2017)剧照。
以我们华东师大为例,我们在闵行校区,夹在虹梅南路和莲花南路两条主干道之间,所以它不太可能在周边打造出可步行的空间。因为两条主干道,大卡车、什么车都在这里面跑,不仅没有办法步行,边上也不可能形成商业区和小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我们去过剑桥或牛津,特别是牛津,一个牛津大学就构成了一个城,那完全是一个以牛津大学为核心所延伸出来的一个城市,所有的东西都是跟大学有关系的,各个学院散落在这个城市里面。我们到了三一学院,是当时以赛亚·伯林在这边做过tutor(导师)的学院。酒吧是托尔金在这边写《魔戒》的时候讨论的酒吧。这就是大学城。我们现在很多大学里会在校园里做很明显的功能化分区,这两者形成一个比较鲜明的对比。
情境主义最初也是有一个理想的。情境主义诞生在巴黎,巴黎也是一个漫步城市,甚至德塞都还有一个说法,他说他喜欢晚上,因为他晚上不睡觉,他有一个自己的巴黎地形图,知道晚上走到什么地方累了,这时候正好有个酒吧是可以休息的。走到另外一个地方,可以坐下来抽烟。这个心理地图只属于他。这些另类的实践都跟这个城市的固有特征是连在一起的。
这里涉及一个城市跟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异化。什么叫异化?就是人造出了这个城市,但是人不得不被所造物所支配。我们现在就被我们的所造物支配,我们肯定有很多美好的理念,但这些理念变成实际之后,好多事情就永远做不成了。情境主义的理想来自20世纪60年代,恰恰来自那个狂飙突进的各种各样的理想都可以试图实践行动的时期。但是到今天情境主义的美好理想和21世纪的现实之间形成了比较大的落差,所以这是我们现在需要面对的真正的问题。
姚嘉伟:刚才罗老师说的,用我们现在大众读者比较熟悉的讲法,就是项飚所谓的“附近的消失”。这本书里有一些内容,跟我们现在的城市规划、城市设计的实践还是蛮相关的。比如说书里写的古典的雅典城,它是一个15分钟可以从这边走到那边的一个城邦,现在正好我们也在宣传所谓的15分钟生活圈,这里面其实是有一些历史经验的再运用之类的,想听听张老师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
张松:刚才罗老师讲的牛津这些古老的城区,慢慢生长,所以它的功能是多元的、混合的,城市是包容的。我们现在一些所谓的大学城,占地几百亩甚至一两千亩,然后里面再功能分区,它跟社会没有关系。归根到底,是观念的一个问题。包括我们现在讲可持续发展,包括主持人讲的15分钟生活圈,也是基于要以人为本,从人们使用便利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这还是观念问题。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个路改小,改成绿化带的,关键是“要不要改”。
像上海这么大的城市,要做到既有的城市存量的规划,且要减量空间,就是要把更多的空间变成绿化生态和人类舒适的环境,而不是造那么多高楼。高楼文化设施还是很漂亮的,但是你走到外面去的街道空间可能就没有那么理想。未来我们也还是要做街道的人性化改造和舒适性改造,包括便利夜间生活方式的一些设计,比如东京的车站,他们原来也是快速路,很宽的,后面改成步行道,而且还考虑到女士出行的需求。往这个方向发展,我觉得未来城市可能真的会越来越好,当然要靠大家共同努力。
城市研究中的中国经验
姚嘉伟:想请陈老师谈一谈,我们阅读城市的历史,对于我们当下的城市生活意味着什么?
陈恒:刚才两位老师都谈得非常好。还是用情境主义的概念来说,有大情境主义和小情境主义。小情境主义是说,所有的城市都有AB面,比如说浦东、浦西、城乡接合部,包括南京路的正面和你翻过去一幢楼的反面,那种差异性是巨大的。如果你不city walk(城市漫步)你发现不了这种差异。这种情景要靠每个人去体验的,这种体验最终会在你心中形成一个大的情景主义的体验。
所谓《命运之城》,命运都是由性格来决定的,城市也有性格,比如说伦敦的理性与秩序,法国巴黎的浪漫与革命,纽约的速度与激情。你读这本书的时候,各个城市都会形成一个概念,它像我们人一样。那么这个性格是怎么去形成的,这是由历史学家去做的事。因为历史学家很擅长综合地看问题,跟做具体事物的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做设计的,关注的是更具体的一些问题。读了这本书,你会对各个城市形成一个基本的判断。反过来,也会更了解我们生活在这个城市中的人。
我读这本书,背后有一个根本的关切:城市的命运究竟走向何方?我感觉这取决于以后人类看待自己和看待这个城市的一个视角。今天这个世界,好像我们人类是唯一的主人。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对这个问题都是打上问号的。是不是应该以生命为中心?这样的话,动物的权利你要考虑。所以这本书最终一个大的结论是,我们在看问题的时候,尤其接受真实的时候,不仅仅要考虑人类,还要考虑动物,还要考虑那些非生命的世界,它都是应该让我们去尊重的,只有这样城市才会和谐地发展下去,人类也才会得以不断地绵延下去。
一只成功挣脱咖啡杯束缚的小刺猬。纪录片《伦敦的动物们》剧照。
姚嘉伟:汤因比的文明史观一方面非常具有开创性,它非常早地跳脱出了西方中心视角来看待全球史。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能看到这本书里囊括的一些东方世界的写作,其实依然是来自西方学者的二手经验。从刚才三位老师讲的从这本书的阅读中带给我们的一些或大或小的实践方法,落到我们自己具身的、一手的、当下的中国经验,这个经验对于我们未来的学术写作或者是城市写作,意味着什么?
陈恒:写作的主体性,我理解就是这个历史的话语权在哪里?20世纪60年代毫无疑问,如果从世界史的角度来讲,在欧美。但是今天中国的发展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汤因比活到今天,他一定会改变写作的思路和整本书的结构。归根到底是一个话语权的问题。对于未来,我们要把这个时代建设好,把新一轮的文明形态想明白是什么样,这样才能获得一个话语权。我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剑桥世界史》总共有七卷九册,这里面的作者将近15%都是中国大陆出去的。如果要放在30年前,这本书的写作可能就只有个别中国人的参与,但现在中国在人才积累方面已经非常多了,而且越来越国际化。
张松:中国人对历史是很重视的,但还是关注书本记载的历史。相比较之下欧洲比较关注这个城市空间的历史。这种理解历史的方式更鲜活、更生动,包括我知道的国外一些历史学者要写三国的故事或者历史,他也会跑到三国遗址这些地方来凭吊,来考古,来考察。真实的历史对文学、历史研究包括各个方面的艺术创作,都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条我觉得西方的艺术家,包括人文学者很关注社会问题。像1962年的《马尔罗法》,1922年意大利克罗齐搞了一部保护自然美景和历史意义的建筑法,他也是大哲学家、历史学家。
罗岗:从《命运之城》这本书里可以看出来,即使在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在汤因比的视野中,中国在整个世界文明中还是扮演了比较重要的角色。比如他提到了龙山文明,这个时候已经开始出现了城市的雏形。但是他说比不上新月地带,比不上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的发展。他也特别提到了安阳,因为20世纪40年代我们就开始有安阳的考古发掘。特别是李济先生写的《安阳》,肯定在当时也有英文本了。
我记得20世纪80年代写文章的时候,总喜欢讲从乡土中国向城市中国转型,即使在那个时候,城市还是一个遥远的未来,或者说还有一个将来的远景。但是随着刚才陈老师和张老师讲的所谓中国的经验重新浮现出来的时候,如果汤因比重新写,他可能会发现中国还有一些很重要的不仅仅是像龙山文化、安阳殷墟或者长安古城的存在。因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类似江南市镇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彭慕兰写的《大分流》认为江南地区跟英格兰地区这两个地方是互相竞争的,也就是说江南地区已经具有了所谓的早期现代的新的雏形。当时中国的江南地区,是农业和商业综合发展的。大分流是因为没有发现煤炭,没有煤炭能源所带来的工业革命,或者叫蒸汽革命。但是如果是从商业的角度来讲,这也意味着江南地区是非常发达的。那么,江南的市镇是一种什么独特的城市形态?这本书里面是没有的。这本书里都是一个个城市,江南市镇不是一个城市,它是一大串城市。在长江、太湖流域,在湖泊江海之间,混杂在其中。我们都知道今天江南有很多古城,这样的一种形态,以及在这里面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的发展,也是文化的发展。明清两代江南地区考取的举人、秀才和状元是最多的。明清的很多文化人、文化名人都从这里出现。如果汤因比能从文明的形态或者文化的形态去把握的话,这又是另外的一个故事了。
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中国的独特经验,或者说独特的城市的存在方式。在我们脑中明清两代中国都是落后的,如果用新的现代化的标准来看的话。就像《万历十五年》讲的,从16世纪中西方就已经开始走不同的道路了,中国就开始停滞了。如果改变这样的一种对现代化的理解,或者说世界史的理解,那么我们中国独特的城市经验,城市形态可能就要被重新书写。作为人类的一种新的存在的方式,可能会给整个人类、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出不同的方案和智慧。
本文经合作方授权刊发。分享嘉宾:陈恒、张松、罗岗 ;主持: 姚嘉伟; 整理 :刘亚光;编辑:Lynn;校对: 杨利 。 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最近微信公众号又改版啦
大家记得将「新京报书评周刊」设置为星标
2024书评周刊合订本上市!
点击书封可即刻下单展鹏配资
涨8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